
著名作家鄧一光;受訪者提供
【文匯網訊】(香港文匯網記者 張帥)一部以1941年香港保衞戰為背景的小說《人,或所有的士兵》,自去年7月出版以來廣受好評。這部長篇小說由著名作家鄧一光歷時五年,多次進出香港,梳理上千萬字圖文史料創作而成。近日,鄧一光接受大公報專訪表示,《人,或所有的士兵》寫的是關於脆弱而需要珍惜的人性故事,「個人」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數字,而是具有溫柔、憂鬱、絕望與恐懼的活生生的人。
「我寫人的弱小,因為我自己就弱小。 鄧一光指出,在主流話語中,時代由精英創造和決定,對渺小的個體而言,他們基本上只是生活在「小而又小」的範疇里,大部分或許孤獨,分裂,沒有同類,完全不同的故事語境,決定了故事的講述對象。
人最可貴是有軟弱和恐懼之心
1941年12月8日,日本在偷襲珍珠港隨後數小時後,揮師三萬餘人撲向香港,歷時十八日,攻陷東方之珠。《人,或所有的士兵》再現了其中的戰爭場景,而且將關注點聚焦在一向被忽視的戰俘身上。
中華民國第7戰區兵站總監部中尉軍需官、D戰俘營戰俘郁漱石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後,被指控「於敵酋俘虜營中屈身事敵,充當傳譯,論落為日本軍國主義之工具」「自墮人格,典身賣命」。郁漱石在法庭陳述「我的確向抓住我的那兩個士兵舉起了雙手,做了他們的俘虜,但是,我沒有背叛」「戰俘比陣亡更加可怕」,自己「只想活着,不要被人蒙上腦袋,拉上絞刑架,脖頸套上發硬的繩索,啟動暗倉,像一枚風乾的果子墜落進長長的暗道」。
小說通過戰俘郁漱石本人的法庭陳述,以及庭審法官、辯護律師和多位證人的多重視角,將那些被戰爭變成「冰冷數字」的個人,重新變成了具有溫柔、憂鬱、絕望與恐懼的活生生的人,喊出「我應該活着!」一個有意思的細節是,小說的封面在設計時將「人」與「士兵」分開,讀者既可以從右往左念成「人,或所有的士兵」,也可以從左往右念為「士兵,或所有的人」。
鄧一光通過小說表達,人最可貴的不是英雄品質,不是理性精神,而是具有軟弱和恐懼之心,這是上蒼給予人類阻止自我毀滅的最後法器,正是因為有了它,人類才有可能,或者說最終不會成為魔鬼。
「有個大家都知道的小故事。柏林牆倒塌前,四名警衞開槍將兩名逃亡者擊斃,柏林牆倒塌後,法庭審理這個案件,律師在法庭上為警衞辯護,聲稱他們是在執行命令,沒有別的選擇,是無罪的。法官認為,作為警衞,不執行上級的命令有罪,但作為心智健全的人,你有將槍口抬高一厘米的權力。」鄧一光在接受大公報採訪中強調,槍口抬高一厘米就是細節,它指認的不是警衞的罪與無罪,而是人之為人的那個奇點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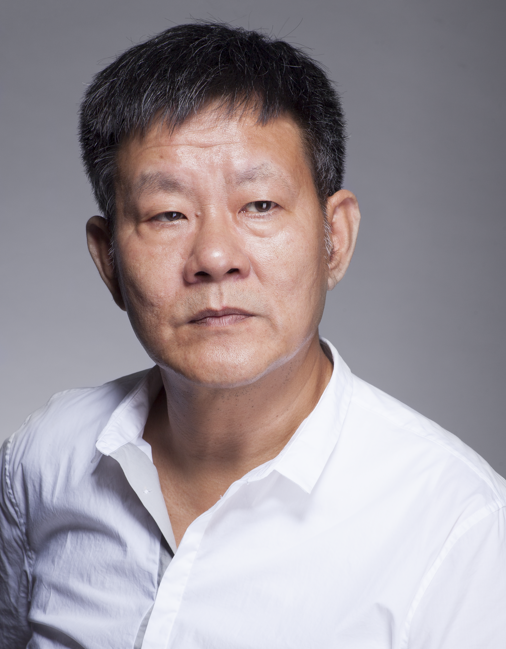
著名作家鄧一光(受訪者提供)
走進人性深處致微致極地帶
鄧一光對一個地方描繪之詳細周全,常讓讀者如身臨其境,印象深刻。為創作《人,或所有的士兵》,鄧一光多次進出香港,翻閱查證了上千萬字的歷史資料,具體到香港十八日保衞戰每天的天氣情況。《人,或所有的士兵》出版後,有讀者閱畢推薦稱:關於香港你想知道的一切,這裏都有。
不過鄧一光對大公報坦率表示:「即使閱讀了大量香港歷史和文化的書籍,在寫這個故事時,我的目的也並不是讓讀者了解香港,甚至不單純是某一段香港歷史,而是人性深處至微至極地帶。」
鄧一光出身於軍人家庭,家中除他之外,兄弟姐妹也都是軍人,戰爭、軍事是他一直鍾情的題材,其叱咤文壇的作品《父親是個兵》《我是太陽》《我是我的神》等均有剛勁硬朗之風。到2009年從武漢遷居到深圳,需要安頓家人、掙錢買房,需要換着法應對潮濕的「回南天」,鄧一光開始重新認識嚴肅的生存環境,建立自己的「城市書寫」方式。
到深圳以後,鄧一光創作了《你可以讓百合生長》《深圳藍》《深圳在北緯22°27′-22°52′》等一系列反映城市人生活的作品,其中既有擁有兩套房地鐵不用轉乘就能到家的「深二代」、加班只是想在老闆面前掙個好印象以後有機會做項目經理的上班族,也有不間斷去獻血站獻血為自己積分落戶的外來青年,和「年好聽,不好過」春節為省錢猶豫再三最後還是放棄回家的打工者。通過走進各色人物內心,鄧一光描寫出城市中不同個體的際遇生活。
警惕「城市書寫」成為沒有生命特質的符號
「城市是由城市人決定的,恐怕你得面對城市人的生命意識和意志這一類比較糾結的問題。我們知道,完全的生命意識和意志通常只存在於精神領域,在以文明規範為特徵的城市,它恰恰是現實與困境的博弈場域。」鄧一光說,城市的語言體系中只有複數,「你們」是什麼,「你們」屬於什麼,但真實的情況是,每一個人都是孤獨的、分裂的,沒有同類。
鄧一光對大公報特別指出,發生在個體「身心分裂」的各種事情,呈現着十分複雜的現代城市生活狀態和面貌,小說家要警惕向群體認知妥協,小心翼翼地捕捉極具特徵性的個體生命認知,完成世界的「個體化」這樣一項審美工作,否則你所希望的「城市書寫」不過是一個沒有生命特質的符號,連稱呼它都不會得到任何有效的回聲。
具體到香港的「城市書寫」,鄧一光說,以香港七百五十萬居民這個數字看,香港的優秀寫作人張袂成陰。上世紀五十年代前,香港就有葉靈鳳和曹聚仁這樣的出色寫作人,以後像劉以鬯、西西、董啟章、也斯、葉輝、鍾曉陽、關麗珊、謝曉虹、陳慧、亦舒、李碧華、梁鳳儀、張小嫻、董橋,黃碧雲、小思、馬家輝、梁文道、鄧小樺等等優秀作家大量湧現,這份名單還可以往下開。而以大陸讀者熟悉香港的武俠文學為例,實際上,除了集大成者金庸,名士梁羽生,玄幻倪匡,他們的書在內地洛陽紙貴,所以大家熟悉,但還有一些清宮、俠情、靈異推理、新派作家也非常棒,內地知道得不多。
鄧一光說:「香港與內地的文學交流一直很冷,有明顯文化隔膜,除了不多幾個學者,內地對香港文學的情況不是很了解。我也是這幾年開始接觸香港文學,只是讀者,談不上經驗。」

著名作家鄧一光;受訪者提供
記錄個體生命「燃燒」是了不起的寫作
2009年南下深圳前,鄧一光在武漢生活了三十年,曾是湖北省作協副主席、武漢市文學院院長,不少湖北作家是他的朋友。今年,因為新冠肺炎疫情武漢受到各界關注。鄧一光原打算清明節回湖北掃墓,因禁足令計劃取消,過段時間想回去看看。
「我有朋友和學生參與了抗擊病毒的工作,我和他們保持着聯繫,其中一位對我說,我很害怕,但我得去救人,救我的家園。」鄧一光說,楚人之祖是祝融,這在荊門包山二號楚墓出土的竹簡中有記載,而楚人的圖騰是鳳凰,武漢人是深知鳳凰涅槃和浴火重生這些詞彙的意義的,那就是武漢人性格的一部分。武漢人在疫情中不唯與病毒搏鬥和全體禁足,人們有勇敢、直面、堅忍、互助和奉獻的一面,也有恐懼、失措、失控、孤獨和絕望的一面,身心靈前所未有的複雜和交集,也正因為如此,人性的豐富和可資信賴才得以彰顯。疫後人們要回到日常生活中,面對的問題太多,如何正視災難和苦難,如何完成哀悼和療愈創傷,如何重拾信任和建立敬畏,這些內容,遠不是「英雄的人民」這個主觀概念角色就能概括。
在鄧一光看來,對災難的敘事極易粗暴化和簡單化,人們應該把宏大歷史思維拆分開,關注一個個的個體生命,因為這座城市真正的內涵,是奠基在無數個體生命之上的;同時,扁平化的「受害者」思維限制了對災難的反思,人們需要進入到災難根源與機理的思考當中,否則不足以告慰人類因災難所經歷的一切。鄧一光坦言,他讀過一些湖北同行在疫情期間的寫作,各種體裁都有,他選擇性看了一部分,有的文字不看也罷,有的文字非常有價值,「面對巨大的災難發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,試圖理性和有效地講述是困難的,作者身處疫情中心,體驗和我完全不同,但我信任他們,準確地說,是敬佩他們的寫作和發聲」。
鄧一光強調,如果說個人的生命體驗中有什麼燃燒劑和黑洞存在,那麼,短短兩個月時間,它們被反覆點燃,在每一秒鐘時間裏不斷轟然爆炸,這實際上是一個心理創傷過程,你本身就是疫情的受害者,還要去傾聽、辨析、澄清、面質和解析,甚至反覆激活和暴露創傷,記錄下屬於人類共同的至暗時刻的驚慌、慘烈、絕望、勇敢、堅忍和捨身奉獻,記錄下個人對疫情的質問和追責,以及初始的理性思考。
「這是非常了不起的寫作和思考行為。」他說。
作家簡介
鄧一光:曾任湖北省作協副主席、武漢市文學院院長,現居深圳。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小說創作,出版長篇小說10部,中短篇小說百餘部,其中《父親是個兵》獲首屆魯迅文學獎,《我是太陽》獲第三屆人民文學獎,《我是我的神》獲第二屆國家圖書獎。2019年出版長篇小說《人,或所有的士兵》,入選中國小說學會2019年度長篇小說排行榜。
責任編輯:Ivy

